[同人] "Belly and I…"
篇名:"Belly and I…"
作者:janusrome
同人:Fringe
配對:William Bell/Walter Bishop
分級:PG-13
聲明:I own nothing.
簡介:偏向角色研究。關於Fringe小組成員的一些片段,以及他們見到的William和Walter。
警告:第一~三季嚴重劇透、第二人稱、第一人稱。
字數:約9,000
A/N:贈云流至他方,2012隨緣居神祕禮物。
人物設定來自前三季的'original timeline',而不是第四季之後的'alternate timeline'。每次看Fringe都覺得很嘴饞,很想要搶Walter的零食吃……
1.
Astrid第一次聽到Walter用「Belly and I…」開始他的句子,當時他們正在調查一起離奇的公車攻擊事件。
「Belly?(肚子?)」她疑惑問道。
「Belly,指的是William Bell。」Peter解釋:「巨大動能的創辦人,這個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和Walter曾經共用實驗室。」
Astrid難掩驚訝,她忍不住瞪著繼續在實驗室裡來回踱步、嘴裡唸唸有詞的Walter。
Astrid擔任Oliva Dunham探員的助理有一段時間了。這是一份和她想像中不太一樣的工作。她從哈佛大學畢業,主修語言學,附修電腦科學,從小著迷於解謎,加入FBI之前修習過密碼學的課程。原本她猜想,她在調查局負責的大概會是分析和解密相關的工作,而不是在哈佛大學Kresge Building的地下室、在養了一頭乳牛的實驗室裡,協助一位瘋癲怪博士處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屍體——或,替他跑腿,為他買各式各樣他突然心生執念,非吃到不可的糖果、甜點或飲料。
她讀過Walter Bishop的檔案,知道他是IQ 196的天才,曾任哈佛大學生物化學系的系主任,發表過許多具有前瞻性的學術論文,在軍方的贊助之下從事諸多邊緣科學領域的研究和實驗。只不過,在一場導致他的助理葬身實驗室火災的意外之後,他依過失殺人罪起訴,由於他的精神狀態判定為不適合受審,因此他被送進聖克萊兒精神病院。在那之後整整十七年的時間,他都待在精神病院。
Astrid不知道Walter「發瘋」之前是怎麼樣的一個人。根據檔案的文字敘述,她捕捉到的是一個聰明絕頂但道德受到質疑的科學家,為了追求學術與科技的突破,他主導過許多飽受爭議的人體實驗。
但今日她見到的Walter沒有半點邪惡科學家的影子。
Walter的神智並非總是清晰,他經常說著除了Peter之外沒人聽得懂的「瘋言瘋語」。Walter老是記不得她的名字,不論她糾正幾次,說她的名字是「Astrid」——而不是Astro或Astral或Astricks或Asteroid——Walter依舊一而再再而三叫錯她的名字。
整體而言,Astrid喜歡Walter,儘管有些時候Walter近乎胡鬧的行徑惹她生氣。Walter有點像是一個頑童,直率、隨心所欲。他經常在案發現場做出某些不合宜的舉動,令他們難堪;但有更多的時候,Astrid羨慕Walter可以自由自在表達自己的好惡和喜怒哀樂——彷彿藉助著一點點的瘋狂,讓他超脫禮儀的束縛,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自由。
大多數的時間Astrid住在實驗室,畢竟辦案期間他們的團隊經常得和時間賽跑。隨著日子推移,她和Walter逐漸變成朋友,甚至於近乎家人的關係。
當Walter和Peter還住在附近旅館的時候,Walter幾乎把實驗室當成家。他的個人物品大部分放在這裡,書、唱片、舊檔案,而他經常在實驗室開火煮東西來吃。
重返三十年前曾經使用過的實驗室勾起了Walter許多回憶。Astrid不斷聽到Walter提起「Belly」的點點滴滴。每次一提到Belly,Walter的雙眼便會發亮,閃爍著少見的光芒。他會用既興奮又緬懷的語調敘述他和Belly一起做過的實驗,某些瘋狂的點子或瘋狂的行徑,抑或他們秉持差異的觀點導致的爭論。
Astrid和多數的人一樣久聞William Bell的大名——同時,她也和多數人一樣,無緣當面見到那位世界名人。不論Walter再怎麼強調Belly和他曾經有多麼親近,Astrid依然有些半信半疑,無法確定William Bell是否也用此生摯友的方式看待Walter。
她不像其他的人到過「另一邊」,沒能在William Bell生前見上他一面。根據他們轉述的事發經過,William Bell為了能讓他們順利從平行世界回到這裡,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。
由於William Bell博士在遺囑中對Walter的敘述以及他將持有的公司股票全數贈予Walter,Astrid確信他們兩人之間確實存在深厚的情誼。那不只是Bell博士留給Walter一大筆財產,其中更有一種交織著補償、道歉和信任的複雜情懷,William Bell把畢生的心血托付給Walter。
Astrid不免有些遺憾,因為她沒能見到那位傳奇人物。然而,在William Bell去世一年之後,她竟有機會親眼一賭Walter和「Belly」共用實驗室的景象——只不過,那個畫面相當詭異,因為William Bell的意識寄居在Oliva的身上。
2.
Olivia第一次聽到「Belly」這個暱稱的時候,她正在開車,載著Bishop父子離開聖克萊兒精神病院。
人們總說,絕望的人會鋌而走險。當她在資料庫裡鍵入「TISSUE DAMAGE」、「CELL CLARIFYING」、「DISSOLVE + FLESH」等關鍵詞,搜尋到Walter Bishop博士的研究報告,Oliva下定決心,不計任何代價都要把那個Walter Bishop找來。原因不僅是那幾份報告顯示疑似有人接續他的研究,使得他成為案件的關係人,更多的動機在於Bishop博士可能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救回John Scott——她的搭檔——性命的人。
627班機的神祕攻擊事件是一個重要的轉折。在那之後Oliva加入國土安全部保護傘下的邊緣部門,調查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匪夷所思犯罪案件。
有一段時間,她的同事、上司兼前輩Charlie Francis相當排斥這些駭人聽聞的新穎犯罪形式,他曾語重心長質疑著,關於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。
和Charlie相較之下,Olivia適應得很快,畢竟,要對抗這些犯罪,她知道自己必須加快腳步學習這些新的知識,因此她沒有時間停下來、沒有時間讓自己質疑這一切。
不過,Olivia同意Charlie的其中一個觀點,那就是他們都無法釋懷「巨大動能」這種私人企業的安全等級竟然高於他們這些聯邦探員,能夠得知並且掌握許多政府的機密資訊——更不用說,許多恐怖攻擊案件使用的科技一再追溯到巨大動能,不禁令人懷疑主導「The Pattern」案件的幕後黑手是否就是這間全球知名的公司。
Olivia希望能和巨大動能的創辦人William Bell博士當面對質,但公司的營運長Nina Sharp卻總是推搪,說Bell博士在旅行無法見她這一類的藉口,令Olivia忍不住懷疑Nina在為涉有重嫌的William Bell掩飾。
然而,不是每一個人都支持Olivia的懷疑。Broyles上校一次又一次駁回她「沒有證據的揣測」,告誡她,除非有實質的證據,否則他們無法約談那位結識不少政府高層、有權有勢的William Bell;更甚者,連Walter都不認為Bell是他們追查的目標,他斬釘截鐵表示,他認識的William雖然是個絕頂聰明又有野心的人,他有很多面向,但恐怖分子絕對不是其中一個。
將近一年的時間,Olivia在迷霧之中打轉。犯下「The Pattern」案件的科學恐怖組織ZFT、ZFT的關鍵成員David Robert Jones——似乎每獲知一條訊息或是鎖定一個關鍵人,他們不但沒能更接近謎底,而倒發現謎團更為複雜。
Olivia萬萬沒有想到是那些案件竟然會牽扯出她的童年。
關於童年往事,她記得的不多,而她總是刻意不去回想那些。那不是什麼快樂的往事,她的繼父喝醉了就對她的母親還有她動粗。直到有一天,她的繼父打斷她的母親的鼻樑,她的忍耐到了極限,她找出繼父的手槍,在他走進家門的時候朝他開了兩槍——那一年,Olivia九歲,她找到了人生的志向:她要保護那些遭受傷害的人。
當Olivia發現自己竟是Cortexiphan藥物試驗的其中一個受試者,以及見到其他受試者的情況,這令她怒不可遏。他們都不是簽了同意書自願參加人體試驗的受試者,而是在他們仍是懞懂無知的幼兒時期,在日間照護中心被「下藥」,不知不覺被當成實驗對象。由於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控制自己的能力,因此不少人的一生就這麼被毀了。
Olivia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對毫無抵抗能力的小孩做出這種事,也不清楚他們到底做了什麼。或許她該感到恐懼,但她只有滿腔怒火,於是她忍不住對Walter發怒,高聲斥責他。
看到Walter在她的面前像個做錯事的小孩一般無助啜泣,喃喃念著他一點都不記得那些往事的時候,Olivia開始感到一絲絲的愧疚。
她知道Walter在「發瘋」之後變了一個人,現在他已經不再是從前的Walter Bishop了。也許她不應該對Walter發脾氣。她的怒氣不應該發洩在一個被判定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身上。
主導Cortexiphan藥物試驗的人是William Bell,他知道所有的答案,同時他也是應該負責的人。這讓Olivia決意非見到他不可。
直到一年之後,Olivia才終於和William Bell面對面——但,不是在他們的世界,而是在「另一邊」。
縱使Olivia的心中有再多的疑問和怒火,穿越空間維度令她的神志有些迷茫,她的憤怒和質疑似乎沒能成功傳達給對方。
William——Bell博士要Olivia這樣叫他——似乎對她的指控不為所動。他道歉,為了那些藥物實驗對他們造成的傷害,但他依然堅持他所做的是必要,那是為了追求知識付出的代價。
她直視著Bell博士。Walter為了某些自己不記得的事情深深懊悔,但William Bell的眼裡沒有半點悔意。她相信自己一點也不喜歡Bell博士。
那次會面講話的人幾乎都是Bell博士。他對Olivia述說了一大堆資訊,而她只能一知半解聽著,盡可能吸收那些關於平行世界的知識。
最後,William向她道歉,對她說離別的時間到了。他牽起她的手,走到窗邊。昏黃的日光照映著他睿智的臉孔,Olivia不喜歡他也不信任他,但她知道,至少他的態度是誠懇的。她告訴自己,她應該要相信William對她說的這番話。
「恐怕,接下來發生的事無可避免……」William說道:「我總是對Walter這麼說:『Physics is a bitch.(物理是個婊子。)』」
3.
Peter第一次聽到他的父親認識鼎鼎大名的William Bell,當時他們正在離開聖克萊兒精神病院的路上。
「唯一真正理解我做什麼的人,只有Belly。」
「誰?」Olivia隨口問道。
「William Bell,以前他和我共用實驗室。」
「William Bell?」Olivia驚訝問道。
「你和巨大動能的創辦人共用實驗室?」Peter忍不住從副駕駛座轉過身,瞪著Walter。
如果那是真的,也未免太諷刺。曾經共用實驗室的兩個人,其中一個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,另一個淪為強制住院的精神病患。
這可真是太好了。
Peter本來在巴格達談生意,卻有個不知打哪冒出來的FBI聯邦探員,好說歹說,甚至用手邊有不利於他的檔案威脅他,希望能夠透過他,去拜訪他那位被關在瘋人院、只有一等親才能探視的父親。
為何如此大費周章?因為有人命在旦夕。
一個替牙膏公司研發配方的化學家哪有這種本領?喔,不,那只是偽裝,其實你的父親在軍方的贊助之下從事邊緣科學的機密研究。
邊緣科學?妳說的其實是偽科學吧?……老天,妳真的相信那些?……等等,妳的意思是,我的父親——那個自我中心、自私自利的天才化學家——其實是弗蘭肯斯坦博士?哇,這可真是越來越精彩了。
Peter百般不願地陪同Olivia前往聖克萊兒精神病院,之後又不情不願簽了字以法律監護人的身分帶Walter出院。
Walter和他記憶中的那個人不太一樣。他的行為十足就是個瘋子。Peter猜想Olivia一定是絕望到了極點,才會尋求Walter的協助。
不過,Peter沒有料想到的是,627班機事件讓他和Walter有機會在實驗室共事,也給了他生平第一次機會認識他的父親。事件結束之後,Walter和他徹夜長談,關於他和William Bell的實驗內容。Walter的神志非常清楚,一點都不像個瘋子。
如果Walter所說是真,那麼日後一定還會發生類似的科學恐怖攻擊事件。Peter的本能告訴他儘快離開波士頓,但探員們需要Walter的學識,而Walter需要他這個監護人的陪同才不會被送回精神病院。
Peter不想和執法機關合作——見鬼,他曾經被逮捕過七次!——也不想留在波士頓以免和他的債主狹路相逢。但事與願違,他依舊留了下來,協助Olivia辦案,以及照顧Walter的日常起居。
Peter看著Walter因為恐怖攻擊案件的手法和他自己曾進行過的研究有關而自責不已,也看著Walter竭力抓住一絲清醒以免被自己的「瘋狂」吞噬。就算Walter為他的生活帶來不少困擾,但Peter卻發現自己無法責備他,同時,他也很難把這個Walter和記憶中的那個形象連結起來。
當他注視著他的父親的時候,他才真正開始思考,整整十七年的時間,Walter到底錯過了什麼、失去了多少。十七個年頭,Peter從來都沒有去聖克萊兒探訪過Walter,他猜想,那一定讓Walter覺得整個世界都遺棄了他。
或許,他決定留下來照顧Walter,一部分的原因出自於內疚,他想要補償他的父親。
Peter很少在一個地方住超過兩個月,但這次回到波士頓他竟然不知不覺住了一年。當他瞭解到自己短時間之內不可能離開這個城市,他開始找公寓,安頓他們父子。Walter一直挑剔他鎖定的房屋資訊,還說什麼他對目前的安排非常滿意。Walter不喜歡離開熟悉環境,這可能也是他堅持回到三十年前使用過的實驗室的原因。倘若Walter堅持睡實驗室或旅館,Peter大概也拿他沒轍——所幸,最後Walter不曉得為何改變了心意,他從Peter選出的資料裡挑出一件,說那一帶是個好地方,許多教授住在那裡,還說:「Belly以前就住在那個街區。」
Belly,又是Belly。William Bell這個名字大概佔了Walter一半的話題,但Walter出院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從來沒有機會見到William Bell。
直到Peter跟隨「Walternate」——他的生父——到了「另一邊」,他才短暫和William Bell相見。由於他們走得非常匆忙,因此他根本沒有時間打量那個世界級的名人,只聽到Bell對他說,Peter小的時候曾經見過他,只是現在Peter不記得了。
那個極短的時間裡發生了很多事,在他們還沒完全搞清楚情況時,Bell和另一個世界就在他們眼前消失——Bell犧牲了自己的生命,使用自己的身體當作能量來源,將他們一行人平安送回到他們原本的世界。
William Bell過世之後,Walter並未停止談論他的朋友。Walter不斷惦念著他需要Belly,因為他沒有Belly那麼聰明,不知道該如何管理Belly留給他的公司,也不知道該如何對抗「Walternate」。
Peter唯一見到他的父親和William相處的模樣,則是在William Bell辭世將近一年之後,某一天,他的「靈魂」——或稱之為「意識」——被召喚回來,附著在Olivia的身上。
說實在話,那個光景超級詭異,但Walter卻樂不可支,一點都不覺得Oliva的臉和聲音說著Bell特有的語調和談話內容有什麼不對勁。見到Walter喜出望外的模樣,Peter擔心自己恐怕是唯一認清到這個情況一點也不正常的人。
果然,事情的發展不如Bell計畫的那麼順利——說真的,怎麼有人會把意識轉移這種事當成理所當然?——在失敗的意識轉移手術之後,Olivia昏迷倒地,被緊急送進醫院。
當醫護人員說除非他們是家屬否則離開病房的時候,Peter急忙說:「她是我的女朋友!」——在那個當下,Peter依稀聽到Walter急切說道:「He’s my partner!」
4.
那是一場夢,惡夢。醒不來的惡夢。現實、幻覺、夢魘,這三者之間的界線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模糊。
或許,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疆界從來都不存在。「Reality is just a matter of perception.(現實只不過是知覺的問題罷了。)」你總是這麼說。
什麼是現實?什麼是幻想?客觀的真實不再存在於你的世界,你剩下的只有腦內世界的瘋狂。
剛來到聖克萊兒的時候,你還會注意日期;但日子一久,時間失去了意義。日期唯一的功能,只剩下標示每天餐點的差異,例如每個星期一的甜點是難吃的奶油糖果布丁。
一直到Olivia前來精神病院探訪,你才終於和這個世界重新建立連結,也終於見到了Peter,你總是掛心不已的獨子。重返三十年前在哈佛的實驗室,重新觸碰實驗儀器,協助探員解決案件,這讓你終於從沉睡的夢境之中醒了過來。
然而,這個世界已經變了——在你「昏睡」於聖克萊兒精神病院的十七年當中。
被人指責是瘋子、用異樣的眼神看著你,那並不是對你最大的打擊;真正動搖了你的,則是你以為自己發瘋,不再相信你自己。在自我否定的絕望之中,Olivia對你的信任猶如一線曙光,讓你一點一點找回對自己的信心。
你從來都不知道原來只是來自另外一個人的信任,就足以改變一切。
離開聖克萊兒之後,你知道你再也不是從前的自己了。你的記憶不連貫,很多東西想不起來、很多東西記不得,你老是在應該熟悉的街區迷路,也總是記不得Peter的電話號碼(你記得數字的組合,卻記不得正確的排序)。當Olivia質問你為什麼拿小孩作實驗的時候,你只能啜泣,不斷道歉,因為你什麼都記不得了。
沒有人知道你有多麼懊悔,也沒有人知道你有多麼挫折。你仰賴他們對你的包容,卻厭惡他們的包容出自於憐憫或同情。你需要他們照顧你,卻討厭他們對你過度關切。
「我一點也不想要像這個樣子。」你曾經這麼說。
不過,Peter卻告訴你,Olivia跟他說過,發瘋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、一個更好的父親。
你不再是昔日那個道德標準令人質疑的天才科學家,你變得更有人性。行過瘋狂的疆域,讓你蛻變為一個更有道德原則、更富情感與關懷的人。
你依舊為過去鑄下的錯誤懺悔,並且承受著來自精神與實質的懲罰——然則,你也開始接受現在的自己,並且努力適應新的生活環境,學習如何獨立自主。
儘管如此,你的心裡卻有個解不開的疙瘩:Belly,William Bell,昔日與你共用實驗室的老友。
你感覺到的並不是嫉妒,而是憤怒,憤怒你的Belly竟然把你一個人丟在瘋人院,獨自創立了巨大動能這間名聞世界的公司。因為……因為,在你的心底,你一直都知道,「你們」終有一天會創立一間公司,把你們的科學知識透過生產的方式擴及到全世界。但巨大動能這間公司的存在卻彷彿甩了你一巴掌,那像是在說著Belly等不及了,拋下了你,獨佔曾屬於你們兩人的夢想。
你可以理解Peter對你不諒解,整整十七年的時間沒有到精神病院探訪過你;但,你卻無法釋懷Belly讓你孤單地在瘋人院裡逐漸腐朽,而他卻享受功成名就的人生。
更不用說,你發現自己「發瘋」的原因竟是Belly切下了你的大腦一部分的左顳葉。
在你出院之後,你和其他想見William Bell的人一樣,都沒有機會親眼見到他。你經常不滿地說,Belly一定在處理幾十億的合約,忙到沒時間見你們。
你有滿腹的疑問想要問Belly,關於這些年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、關於ZFT、關於另一個世界、關於變形者、關於……他為什麼切下你的大腦把你搞瘋。
但怎麼也沒有想到,睽違十幾年的光陰,當Belly和你在「另一邊」重逢,那竟標示著訣別。
5.
你站在醫院急診室的入口,滿面怒容。「哈囉,William,」你說,聲音裡充滿敵意:「我看到你變老了。」
我瞪著你,回道:「看來我不是唯一的人。」
……Walter,我親愛的老朋友,我知道你有很多疑問,但我卻發現沒有足夠的時間回答你所有的問題。
你還記得我們的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嗎?……不管怎樣,至少,我記得很清楚。
那是1974年,當時我只有二十歲,還是個學生;而你,你比我大七歲,卻已經是哈佛的教授。
那是一個初秋的晚上,我獨自留在空蕩蕩的教室裡,一面聽著Sly Stone的音樂,一面試圖解開黑板上的Morianz Equation。我不知道自己在黑板前面站了多久,只知道我依然解不開算式,而煙灰缸裡已經堆滿小山一般的煙屁股。
直到音樂戛然而止,我才突然回過神。我轉過身,看到你站在我的身後,把我放在講桌上的手提音響電源切斷,說音樂吵得你無法專心工作。當我正要開口指責你的時候,你卻逕自走到黑板前,拿起粉筆,解開了那個全世界只有五個人解出的方程式。
那個方程式讓我苦苦思索了一整個晚上仍不得其解,但你卻只費了幾分鐘的時間就寫出了證明的算式。在那之後,你還不以為意地對我說:「喔,那我大概是第六個人了。」
那讓我立刻認出你。
你是Walter Bishop,據信可能是繼愛因斯坦之後本世紀另一個偉大的科學家。
「我一直想見你!」我忍不住說。
你隨口回答:「好啦,現在你見到我了。」說完,你頭也不回離開,把我獨自留在空無一人的教室裡。
那晚之後,我仍經常播放那張卡帶——只不過,原本能讓我專心的音樂,卻只會讓我分心,因為那些旋律總是把我帶回我們相遇的空教室。
我出席了你在MIT舉辦的講座。
你說,如果能夠透過某種界面,把人類的大腦像內部互聯網的電腦那樣連結起來,我們就能在一個小時之內接受到另一個人花費了數年收集到的資訊。你的研究令我著迷不已。有許多人批評你的論點是不切實際的幻想,還抨擊道:「那是科幻,不是科學。」——然而,我卻認為,影響未來一、兩個世代的科學突破,在當代通常都會被判定為不可能實現的空想。
領著我進入邊緣科學領域的人正是你,Walter。唸書的時候我在你的實驗室當你的助理,等到我取得學位之後,我依然以同事的身分留在你的實驗室,和你一起工作。
我還記得你和我第一次一起踏上「acid trip」的時候,你把方糖放進嘴裡,接著往後躺進擺在實驗室角落的單人沙發。當LSD開始影響你的大腦,你告訴我,你對我的第一印象其實不是很好,因為你覺得我「輕挑」。
嘿,Bishop教授,別忘了當時我只是個二十歲的學生哪。
回想起來,我在認識你之後才開始聽古典音樂和歌劇。有一次,你甚至要我戴上偵測腦波的儀器,試圖向我證明和聲音樂對於腦波的影響。
儘管如此,我還是繼續聽搖滾樂。
我總是一直注視著你,Walter,就算我介紹你認識了Elizabeth,而你穿著紫色燕尾服和她結婚,我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瞭解你、理解你的研究和實驗的人。
就算你有了家庭、有了小孩,你依舊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實驗室。你在我身邊的時間遠超過和你的家人相處的時間。
你和我曾經談論過好幾次,以後不再接軍方的委託研究之後,要創立自己的公司。
那聽起來非常美好,直到……Peter生病。
很遺憾我沒有出席Peter的葬禮。但Walter,你知道嗎?在你廢寢忘食研究解藥的時候,維持我們實驗室繼續運作的人,只有我。我必須打起精神,參加所有的軍事及商業會議,並且扛下手邊全部的委託案件——畢竟,那是我能夠協助你的方式。
我猜想,一定是我太忙以致於太過大意,等我接到Nina的電話,已經為時已晚,來不及趕回去阻止你跨越到「另一邊」。
如今回頭去看,那絕對是我們一生的轉捩點。
由於你違反了物理法則跨越了空間的界線,我們的世界和另一個平行世界變得不太穩定。你無法用原本的裝置把Peter送回家,我們必須找到別的方法,因此才會在兒童的身上進行Cortexiphan藥物試驗,讓他們在不撕裂空間結構的前提之下把Peter平安送回去。
只可惜,那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困難許多。最後Cortexiphan藥物試驗宣布失敗,全面中止,Peter也留了下來,沒有人再提及要把Peter送回「家」這件事。
Walter,你問我為什麼切下你的大腦?……我想,那表示你不記得了……真相,Walter,是你央求我這麼做的。你要我切除你左顳葉的部分海馬迴,移除你發明跨越空間儀器的記憶,以免你再造成更多的傷害,防止你變成你害怕自己成為的那個人。
你是一個擁有無人能及的異想天開想像力的天才,Walter,但我卻親手把你送進精神病院。
我曾經到聖克萊兒探望過你,前前後後一共六次。只不過,你的精神狀況不是很穩定,我猜想你大概不記得那些會面的情形。
此後,我大部分的時間停留在「另一邊」,試圖補救你穿越平行世界所造成的損害。
我想,最終,你我都得為我們所做的事、造成的後果付出代價。
最後一次見到你的時候,我的肉體已經死去,殘存的只有意識。
儘管這仍是我計畫之中的事,但能夠和你再度共用實驗室,我得承認那帶給我超乎預期的愉悅。
你從收藏的黑膠唱片裡找出Supertramp在1977年發行的專輯。我不確定這是當年我送你的那張唱片,還是後來你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。
我看著你吞雲吐霧,從你的手上接過我們共享的那根香煙。
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,在我們還很年輕的時候,有一次,你看到我在捲大麻煙,你說你從來沒有這樣抽過大麻。我知道你通常用的是水煙斗,所以我笑說那是因為你不會捲煙的緣故。
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會說出那句話:「我猜,你也從來沒有這樣抽過。」語畢,我小心翼翼反叼住煙,避免點燃的煙頭燙到自己,同時朝你靠近。
你沒有猶豫,湊了過來。當你含住捲煙吸氣的時候,你的嘴唇和我的嘴唇輕輕相碰。
我猜你從來都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。
實驗室的母牛Gene適時哞了一聲,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把我帶離回憶。
我隔著眼鏡瞪著牠,想到除了腦死的病患之外,或許牠也能成為我的意識的宿主。
「William?」你盯著我,彷彿一瞬間看穿我的念頭。
我們相視而笑。
「……就算我們能夠成功把你的意識轉移到Gene身上,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得考慮。」你一面順著母牛的毛,一面對我說。
「我們可以透過腦波溝通,」我回道:「你得把我接上腦電圖的儀器,解讀我的思維。」
「就算那行得通,然而……我還是得幫你擠奶。」
我盯著你憋笑的臉,說:「我們可以指派Astrid。」
我們再度相視而笑。
Walter,我相信你一定記得我從來就不喜歡說再見。
我想,等到我消失之後,你才會發覺這就是我說再見的方式。
我所求的,其實並不多……
A/N2:William Bell和Walter Bishop相遇的場景改寫自官漫內容,當時Bell在聽的歌是Sly Stone的'Thank You'。
#317,Walter和Bell!Olivia在實驗室,背景音樂就是'Give A Little Bit'。
Fringe的主要角色我都滿喜歡,雖然第四季已經被我直接歸為爛尾作,但我想我還是會找時間補完第五季,有始有終。而且John Noble的演技相當棒,看他演Walter本身就是一種享受。
第二季季末,Walter和Bell在速食店鬥嘴那段讓我在螢幕前翻滾,差不多奠定了我支持他們的立場。我應該自首說我的另外一艘船是Nina/Olivia嗎?看來我真的很喜歡「老朋友」這種設定。
作者:janusrome
同人:Fringe
配對:William Bell/Walter Bishop
分級:PG-13
聲明:I own nothing.
簡介:偏向角色研究。關於Fringe小組成員的一些片段,以及他們見到的William和Walter。
警告:第一~三季嚴重劇透、第二人稱、第一人稱。
字數:約9,000
A/N:贈云流至他方,2012隨緣居神祕禮物。
人物設定來自前三季的'original timeline',而不是第四季之後的'alternate timeline'。每次看Fringe都覺得很嘴饞,很想要搶Walter的零食吃……
1.
Astrid第一次聽到Walter用「Belly and I…」開始他的句子,當時他們正在調查一起離奇的公車攻擊事件。
「Belly?(肚子?)」她疑惑問道。
「Belly,指的是William Bell。」Peter解釋:「巨大動能的創辦人,這個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和Walter曾經共用實驗室。」
Astrid難掩驚訝,她忍不住瞪著繼續在實驗室裡來回踱步、嘴裡唸唸有詞的Walter。
Astrid擔任Oliva Dunham探員的助理有一段時間了。這是一份和她想像中不太一樣的工作。她從哈佛大學畢業,主修語言學,附修電腦科學,從小著迷於解謎,加入FBI之前修習過密碼學的課程。原本她猜想,她在調查局負責的大概會是分析和解密相關的工作,而不是在哈佛大學Kresge Building的地下室、在養了一頭乳牛的實驗室裡,協助一位瘋癲怪博士處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屍體——或,替他跑腿,為他買各式各樣他突然心生執念,非吃到不可的糖果、甜點或飲料。
她讀過Walter Bishop的檔案,知道他是IQ 196的天才,曾任哈佛大學生物化學系的系主任,發表過許多具有前瞻性的學術論文,在軍方的贊助之下從事諸多邊緣科學領域的研究和實驗。只不過,在一場導致他的助理葬身實驗室火災的意外之後,他依過失殺人罪起訴,由於他的精神狀態判定為不適合受審,因此他被送進聖克萊兒精神病院。在那之後整整十七年的時間,他都待在精神病院。
Astrid不知道Walter「發瘋」之前是怎麼樣的一個人。根據檔案的文字敘述,她捕捉到的是一個聰明絕頂但道德受到質疑的科學家,為了追求學術與科技的突破,他主導過許多飽受爭議的人體實驗。
但今日她見到的Walter沒有半點邪惡科學家的影子。
Walter的神智並非總是清晰,他經常說著除了Peter之外沒人聽得懂的「瘋言瘋語」。Walter老是記不得她的名字,不論她糾正幾次,說她的名字是「Astrid」——而不是Astro或Astral或Astricks或Asteroid——Walter依舊一而再再而三叫錯她的名字。
整體而言,Astrid喜歡Walter,儘管有些時候Walter近乎胡鬧的行徑惹她生氣。Walter有點像是一個頑童,直率、隨心所欲。他經常在案發現場做出某些不合宜的舉動,令他們難堪;但有更多的時候,Astrid羨慕Walter可以自由自在表達自己的好惡和喜怒哀樂——彷彿藉助著一點點的瘋狂,讓他超脫禮儀的束縛,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自由。
大多數的時間Astrid住在實驗室,畢竟辦案期間他們的團隊經常得和時間賽跑。隨著日子推移,她和Walter逐漸變成朋友,甚至於近乎家人的關係。
當Walter和Peter還住在附近旅館的時候,Walter幾乎把實驗室當成家。他的個人物品大部分放在這裡,書、唱片、舊檔案,而他經常在實驗室開火煮東西來吃。
重返三十年前曾經使用過的實驗室勾起了Walter許多回憶。Astrid不斷聽到Walter提起「Belly」的點點滴滴。每次一提到Belly,Walter的雙眼便會發亮,閃爍著少見的光芒。他會用既興奮又緬懷的語調敘述他和Belly一起做過的實驗,某些瘋狂的點子或瘋狂的行徑,抑或他們秉持差異的觀點導致的爭論。
Astrid和多數的人一樣久聞William Bell的大名——同時,她也和多數人一樣,無緣當面見到那位世界名人。不論Walter再怎麼強調Belly和他曾經有多麼親近,Astrid依然有些半信半疑,無法確定William Bell是否也用此生摯友的方式看待Walter。
她不像其他的人到過「另一邊」,沒能在William Bell生前見上他一面。根據他們轉述的事發經過,William Bell為了能讓他們順利從平行世界回到這裡,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。
由於William Bell博士在遺囑中對Walter的敘述以及他將持有的公司股票全數贈予Walter,Astrid確信他們兩人之間確實存在深厚的情誼。那不只是Bell博士留給Walter一大筆財產,其中更有一種交織著補償、道歉和信任的複雜情懷,William Bell把畢生的心血托付給Walter。
Astrid不免有些遺憾,因為她沒能見到那位傳奇人物。然而,在William Bell去世一年之後,她竟有機會親眼一賭Walter和「Belly」共用實驗室的景象——只不過,那個畫面相當詭異,因為William Bell的意識寄居在Oliva的身上。
2.
Olivia第一次聽到「Belly」這個暱稱的時候,她正在開車,載著Bishop父子離開聖克萊兒精神病院。
人們總說,絕望的人會鋌而走險。當她在資料庫裡鍵入「TISSUE DAMAGE」、「CELL CLARIFYING」、「DISSOLVE + FLESH」等關鍵詞,搜尋到Walter Bishop博士的研究報告,Oliva下定決心,不計任何代價都要把那個Walter Bishop找來。原因不僅是那幾份報告顯示疑似有人接續他的研究,使得他成為案件的關係人,更多的動機在於Bishop博士可能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救回John Scott——她的搭檔——性命的人。
627班機的神祕攻擊事件是一個重要的轉折。在那之後Oliva加入國土安全部保護傘下的邊緣部門,調查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匪夷所思犯罪案件。
有一段時間,她的同事、上司兼前輩Charlie Francis相當排斥這些駭人聽聞的新穎犯罪形式,他曾語重心長質疑著,關於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。
和Charlie相較之下,Olivia適應得很快,畢竟,要對抗這些犯罪,她知道自己必須加快腳步學習這些新的知識,因此她沒有時間停下來、沒有時間讓自己質疑這一切。
不過,Olivia同意Charlie的其中一個觀點,那就是他們都無法釋懷「巨大動能」這種私人企業的安全等級竟然高於他們這些聯邦探員,能夠得知並且掌握許多政府的機密資訊——更不用說,許多恐怖攻擊案件使用的科技一再追溯到巨大動能,不禁令人懷疑主導「The Pattern」案件的幕後黑手是否就是這間全球知名的公司。
Olivia希望能和巨大動能的創辦人William Bell博士當面對質,但公司的營運長Nina Sharp卻總是推搪,說Bell博士在旅行無法見她這一類的藉口,令Olivia忍不住懷疑Nina在為涉有重嫌的William Bell掩飾。
然而,不是每一個人都支持Olivia的懷疑。Broyles上校一次又一次駁回她「沒有證據的揣測」,告誡她,除非有實質的證據,否則他們無法約談那位結識不少政府高層、有權有勢的William Bell;更甚者,連Walter都不認為Bell是他們追查的目標,他斬釘截鐵表示,他認識的William雖然是個絕頂聰明又有野心的人,他有很多面向,但恐怖分子絕對不是其中一個。
將近一年的時間,Olivia在迷霧之中打轉。犯下「The Pattern」案件的科學恐怖組織ZFT、ZFT的關鍵成員David Robert Jones——似乎每獲知一條訊息或是鎖定一個關鍵人,他們不但沒能更接近謎底,而倒發現謎團更為複雜。
Olivia萬萬沒有想到是那些案件竟然會牽扯出她的童年。
關於童年往事,她記得的不多,而她總是刻意不去回想那些。那不是什麼快樂的往事,她的繼父喝醉了就對她的母親還有她動粗。直到有一天,她的繼父打斷她的母親的鼻樑,她的忍耐到了極限,她找出繼父的手槍,在他走進家門的時候朝他開了兩槍——那一年,Olivia九歲,她找到了人生的志向:她要保護那些遭受傷害的人。
當Olivia發現自己竟是Cortexiphan藥物試驗的其中一個受試者,以及見到其他受試者的情況,這令她怒不可遏。他們都不是簽了同意書自願參加人體試驗的受試者,而是在他們仍是懞懂無知的幼兒時期,在日間照護中心被「下藥」,不知不覺被當成實驗對象。由於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控制自己的能力,因此不少人的一生就這麼被毀了。
Olivia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對毫無抵抗能力的小孩做出這種事,也不清楚他們到底做了什麼。或許她該感到恐懼,但她只有滿腔怒火,於是她忍不住對Walter發怒,高聲斥責他。
看到Walter在她的面前像個做錯事的小孩一般無助啜泣,喃喃念著他一點都不記得那些往事的時候,Olivia開始感到一絲絲的愧疚。
她知道Walter在「發瘋」之後變了一個人,現在他已經不再是從前的Walter Bishop了。也許她不應該對Walter發脾氣。她的怒氣不應該發洩在一個被判定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身上。
主導Cortexiphan藥物試驗的人是William Bell,他知道所有的答案,同時他也是應該負責的人。這讓Olivia決意非見到他不可。
直到一年之後,Olivia才終於和William Bell面對面——但,不是在他們的世界,而是在「另一邊」。
縱使Olivia的心中有再多的疑問和怒火,穿越空間維度令她的神志有些迷茫,她的憤怒和質疑似乎沒能成功傳達給對方。
William——Bell博士要Olivia這樣叫他——似乎對她的指控不為所動。他道歉,為了那些藥物實驗對他們造成的傷害,但他依然堅持他所做的是必要,那是為了追求知識付出的代價。
她直視著Bell博士。Walter為了某些自己不記得的事情深深懊悔,但William Bell的眼裡沒有半點悔意。她相信自己一點也不喜歡Bell博士。
那次會面講話的人幾乎都是Bell博士。他對Olivia述說了一大堆資訊,而她只能一知半解聽著,盡可能吸收那些關於平行世界的知識。
最後,William向她道歉,對她說離別的時間到了。他牽起她的手,走到窗邊。昏黃的日光照映著他睿智的臉孔,Olivia不喜歡他也不信任他,但她知道,至少他的態度是誠懇的。她告訴自己,她應該要相信William對她說的這番話。
「恐怕,接下來發生的事無可避免……」William說道:「我總是對Walter這麼說:『Physics is a bitch.(物理是個婊子。)』」
3.
Peter第一次聽到他的父親認識鼎鼎大名的William Bell,當時他們正在離開聖克萊兒精神病院的路上。
「唯一真正理解我做什麼的人,只有Belly。」
「誰?」Olivia隨口問道。
「William Bell,以前他和我共用實驗室。」
「William Bell?」Olivia驚訝問道。
「你和巨大動能的創辦人共用實驗室?」Peter忍不住從副駕駛座轉過身,瞪著Walter。
如果那是真的,也未免太諷刺。曾經共用實驗室的兩個人,其中一個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,另一個淪為強制住院的精神病患。
這可真是太好了。
Peter本來在巴格達談生意,卻有個不知打哪冒出來的FBI聯邦探員,好說歹說,甚至用手邊有不利於他的檔案威脅他,希望能夠透過他,去拜訪他那位被關在瘋人院、只有一等親才能探視的父親。
為何如此大費周章?因為有人命在旦夕。
一個替牙膏公司研發配方的化學家哪有這種本領?喔,不,那只是偽裝,其實你的父親在軍方的贊助之下從事邊緣科學的機密研究。
邊緣科學?妳說的其實是偽科學吧?……老天,妳真的相信那些?……等等,妳的意思是,我的父親——那個自我中心、自私自利的天才化學家——其實是弗蘭肯斯坦博士?哇,這可真是越來越精彩了。
Peter百般不願地陪同Olivia前往聖克萊兒精神病院,之後又不情不願簽了字以法律監護人的身分帶Walter出院。
Walter和他記憶中的那個人不太一樣。他的行為十足就是個瘋子。Peter猜想Olivia一定是絕望到了極點,才會尋求Walter的協助。
不過,Peter沒有料想到的是,627班機事件讓他和Walter有機會在實驗室共事,也給了他生平第一次機會認識他的父親。事件結束之後,Walter和他徹夜長談,關於他和William Bell的實驗內容。Walter的神志非常清楚,一點都不像個瘋子。
如果Walter所說是真,那麼日後一定還會發生類似的科學恐怖攻擊事件。Peter的本能告訴他儘快離開波士頓,但探員們需要Walter的學識,而Walter需要他這個監護人的陪同才不會被送回精神病院。
Peter不想和執法機關合作——見鬼,他曾經被逮捕過七次!——也不想留在波士頓以免和他的債主狹路相逢。但事與願違,他依舊留了下來,協助Olivia辦案,以及照顧Walter的日常起居。
Peter看著Walter因為恐怖攻擊案件的手法和他自己曾進行過的研究有關而自責不已,也看著Walter竭力抓住一絲清醒以免被自己的「瘋狂」吞噬。就算Walter為他的生活帶來不少困擾,但Peter卻發現自己無法責備他,同時,他也很難把這個Walter和記憶中的那個形象連結起來。
當他注視著他的父親的時候,他才真正開始思考,整整十七年的時間,Walter到底錯過了什麼、失去了多少。十七個年頭,Peter從來都沒有去聖克萊兒探訪過Walter,他猜想,那一定讓Walter覺得整個世界都遺棄了他。
或許,他決定留下來照顧Walter,一部分的原因出自於內疚,他想要補償他的父親。
Peter很少在一個地方住超過兩個月,但這次回到波士頓他竟然不知不覺住了一年。當他瞭解到自己短時間之內不可能離開這個城市,他開始找公寓,安頓他們父子。Walter一直挑剔他鎖定的房屋資訊,還說什麼他對目前的安排非常滿意。Walter不喜歡離開熟悉環境,這可能也是他堅持回到三十年前使用過的實驗室的原因。倘若Walter堅持睡實驗室或旅館,Peter大概也拿他沒轍——所幸,最後Walter不曉得為何改變了心意,他從Peter選出的資料裡挑出一件,說那一帶是個好地方,許多教授住在那裡,還說:「Belly以前就住在那個街區。」
Belly,又是Belly。William Bell這個名字大概佔了Walter一半的話題,但Walter出院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從來沒有機會見到William Bell。
直到Peter跟隨「Walternate」——他的生父——到了「另一邊」,他才短暫和William Bell相見。由於他們走得非常匆忙,因此他根本沒有時間打量那個世界級的名人,只聽到Bell對他說,Peter小的時候曾經見過他,只是現在Peter不記得了。
那個極短的時間裡發生了很多事,在他們還沒完全搞清楚情況時,Bell和另一個世界就在他們眼前消失——Bell犧牲了自己的生命,使用自己的身體當作能量來源,將他們一行人平安送回到他們原本的世界。
William Bell過世之後,Walter並未停止談論他的朋友。Walter不斷惦念著他需要Belly,因為他沒有Belly那麼聰明,不知道該如何管理Belly留給他的公司,也不知道該如何對抗「Walternate」。
Peter唯一見到他的父親和William相處的模樣,則是在William Bell辭世將近一年之後,某一天,他的「靈魂」——或稱之為「意識」——被召喚回來,附著在Olivia的身上。
說實在話,那個光景超級詭異,但Walter卻樂不可支,一點都不覺得Oliva的臉和聲音說著Bell特有的語調和談話內容有什麼不對勁。見到Walter喜出望外的模樣,Peter擔心自己恐怕是唯一認清到這個情況一點也不正常的人。
果然,事情的發展不如Bell計畫的那麼順利——說真的,怎麼有人會把意識轉移這種事當成理所當然?——在失敗的意識轉移手術之後,Olivia昏迷倒地,被緊急送進醫院。
當醫護人員說除非他們是家屬否則離開病房的時候,Peter急忙說:「她是我的女朋友!」——在那個當下,Peter依稀聽到Walter急切說道:「He’s my partner!」
4.
那是一場夢,惡夢。醒不來的惡夢。現實、幻覺、夢魘,這三者之間的界線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模糊。
或許,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疆界從來都不存在。「Reality is just a matter of perception.(現實只不過是知覺的問題罷了。)」你總是這麼說。
什麼是現實?什麼是幻想?客觀的真實不再存在於你的世界,你剩下的只有腦內世界的瘋狂。
剛來到聖克萊兒的時候,你還會注意日期;但日子一久,時間失去了意義。日期唯一的功能,只剩下標示每天餐點的差異,例如每個星期一的甜點是難吃的奶油糖果布丁。
一直到Olivia前來精神病院探訪,你才終於和這個世界重新建立連結,也終於見到了Peter,你總是掛心不已的獨子。重返三十年前在哈佛的實驗室,重新觸碰實驗儀器,協助探員解決案件,這讓你終於從沉睡的夢境之中醒了過來。
然而,這個世界已經變了——在你「昏睡」於聖克萊兒精神病院的十七年當中。
被人指責是瘋子、用異樣的眼神看著你,那並不是對你最大的打擊;真正動搖了你的,則是你以為自己發瘋,不再相信你自己。在自我否定的絕望之中,Olivia對你的信任猶如一線曙光,讓你一點一點找回對自己的信心。
你從來都不知道原來只是來自另外一個人的信任,就足以改變一切。
離開聖克萊兒之後,你知道你再也不是從前的自己了。你的記憶不連貫,很多東西想不起來、很多東西記不得,你老是在應該熟悉的街區迷路,也總是記不得Peter的電話號碼(你記得數字的組合,卻記不得正確的排序)。當Olivia質問你為什麼拿小孩作實驗的時候,你只能啜泣,不斷道歉,因為你什麼都記不得了。
沒有人知道你有多麼懊悔,也沒有人知道你有多麼挫折。你仰賴他們對你的包容,卻厭惡他們的包容出自於憐憫或同情。你需要他們照顧你,卻討厭他們對你過度關切。
「我一點也不想要像這個樣子。」你曾經這麼說。
不過,Peter卻告訴你,Olivia跟他說過,發瘋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、一個更好的父親。
你不再是昔日那個道德標準令人質疑的天才科學家,你變得更有人性。行過瘋狂的疆域,讓你蛻變為一個更有道德原則、更富情感與關懷的人。
你依舊為過去鑄下的錯誤懺悔,並且承受著來自精神與實質的懲罰——然則,你也開始接受現在的自己,並且努力適應新的生活環境,學習如何獨立自主。
儘管如此,你的心裡卻有個解不開的疙瘩:Belly,William Bell,昔日與你共用實驗室的老友。
你感覺到的並不是嫉妒,而是憤怒,憤怒你的Belly竟然把你一個人丟在瘋人院,獨自創立了巨大動能這間名聞世界的公司。因為……因為,在你的心底,你一直都知道,「你們」終有一天會創立一間公司,把你們的科學知識透過生產的方式擴及到全世界。但巨大動能這間公司的存在卻彷彿甩了你一巴掌,那像是在說著Belly等不及了,拋下了你,獨佔曾屬於你們兩人的夢想。
你可以理解Peter對你不諒解,整整十七年的時間沒有到精神病院探訪過你;但,你卻無法釋懷Belly讓你孤單地在瘋人院裡逐漸腐朽,而他卻享受功成名就的人生。
更不用說,你發現自己「發瘋」的原因竟是Belly切下了你的大腦一部分的左顳葉。
在你出院之後,你和其他想見William Bell的人一樣,都沒有機會親眼見到他。你經常不滿地說,Belly一定在處理幾十億的合約,忙到沒時間見你們。
你有滿腹的疑問想要問Belly,關於這些年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、關於ZFT、關於另一個世界、關於變形者、關於……他為什麼切下你的大腦把你搞瘋。
但怎麼也沒有想到,睽違十幾年的光陰,當Belly和你在「另一邊」重逢,那竟標示著訣別。
5.
你站在醫院急診室的入口,滿面怒容。「哈囉,William,」你說,聲音裡充滿敵意:「我看到你變老了。」
我瞪著你,回道:「看來我不是唯一的人。」
……Walter,我親愛的老朋友,我知道你有很多疑問,但我卻發現沒有足夠的時間回答你所有的問題。
你還記得我們的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嗎?……不管怎樣,至少,我記得很清楚。
那是1974年,當時我只有二十歲,還是個學生;而你,你比我大七歲,卻已經是哈佛的教授。
那是一個初秋的晚上,我獨自留在空蕩蕩的教室裡,一面聽著Sly Stone的音樂,一面試圖解開黑板上的Morianz Equation。我不知道自己在黑板前面站了多久,只知道我依然解不開算式,而煙灰缸裡已經堆滿小山一般的煙屁股。
直到音樂戛然而止,我才突然回過神。我轉過身,看到你站在我的身後,把我放在講桌上的手提音響電源切斷,說音樂吵得你無法專心工作。當我正要開口指責你的時候,你卻逕自走到黑板前,拿起粉筆,解開了那個全世界只有五個人解出的方程式。
那個方程式讓我苦苦思索了一整個晚上仍不得其解,但你卻只費了幾分鐘的時間就寫出了證明的算式。在那之後,你還不以為意地對我說:「喔,那我大概是第六個人了。」
那讓我立刻認出你。
你是Walter Bishop,據信可能是繼愛因斯坦之後本世紀另一個偉大的科學家。
「我一直想見你!」我忍不住說。
你隨口回答:「好啦,現在你見到我了。」說完,你頭也不回離開,把我獨自留在空無一人的教室裡。
那晚之後,我仍經常播放那張卡帶——只不過,原本能讓我專心的音樂,卻只會讓我分心,因為那些旋律總是把我帶回我們相遇的空教室。
我出席了你在MIT舉辦的講座。
你說,如果能夠透過某種界面,把人類的大腦像內部互聯網的電腦那樣連結起來,我們就能在一個小時之內接受到另一個人花費了數年收集到的資訊。你的研究令我著迷不已。有許多人批評你的論點是不切實際的幻想,還抨擊道:「那是科幻,不是科學。」——然而,我卻認為,影響未來一、兩個世代的科學突破,在當代通常都會被判定為不可能實現的空想。
領著我進入邊緣科學領域的人正是你,Walter。唸書的時候我在你的實驗室當你的助理,等到我取得學位之後,我依然以同事的身分留在你的實驗室,和你一起工作。
我還記得你和我第一次一起踏上「acid trip」的時候,你把方糖放進嘴裡,接著往後躺進擺在實驗室角落的單人沙發。當LSD開始影響你的大腦,你告訴我,你對我的第一印象其實不是很好,因為你覺得我「輕挑」。
嘿,Bishop教授,別忘了當時我只是個二十歲的學生哪。
回想起來,我在認識你之後才開始聽古典音樂和歌劇。有一次,你甚至要我戴上偵測腦波的儀器,試圖向我證明和聲音樂對於腦波的影響。
儘管如此,我還是繼續聽搖滾樂。
我總是一直注視著你,Walter,就算我介紹你認識了Elizabeth,而你穿著紫色燕尾服和她結婚,我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瞭解你、理解你的研究和實驗的人。
就算你有了家庭、有了小孩,你依舊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實驗室。你在我身邊的時間遠超過和你的家人相處的時間。
你和我曾經談論過好幾次,以後不再接軍方的委託研究之後,要創立自己的公司。
那聽起來非常美好,直到……Peter生病。
很遺憾我沒有出席Peter的葬禮。但Walter,你知道嗎?在你廢寢忘食研究解藥的時候,維持我們實驗室繼續運作的人,只有我。我必須打起精神,參加所有的軍事及商業會議,並且扛下手邊全部的委託案件——畢竟,那是我能夠協助你的方式。
我猜想,一定是我太忙以致於太過大意,等我接到Nina的電話,已經為時已晚,來不及趕回去阻止你跨越到「另一邊」。
如今回頭去看,那絕對是我們一生的轉捩點。
由於你違反了物理法則跨越了空間的界線,我們的世界和另一個平行世界變得不太穩定。你無法用原本的裝置把Peter送回家,我們必須找到別的方法,因此才會在兒童的身上進行Cortexiphan藥物試驗,讓他們在不撕裂空間結構的前提之下把Peter平安送回去。
只可惜,那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困難許多。最後Cortexiphan藥物試驗宣布失敗,全面中止,Peter也留了下來,沒有人再提及要把Peter送回「家」這件事。
Walter,你問我為什麼切下你的大腦?……我想,那表示你不記得了……真相,Walter,是你央求我這麼做的。你要我切除你左顳葉的部分海馬迴,移除你發明跨越空間儀器的記憶,以免你再造成更多的傷害,防止你變成你害怕自己成為的那個人。
你是一個擁有無人能及的異想天開想像力的天才,Walter,但我卻親手把你送進精神病院。
我曾經到聖克萊兒探望過你,前前後後一共六次。只不過,你的精神狀況不是很穩定,我猜想你大概不記得那些會面的情形。
此後,我大部分的時間停留在「另一邊」,試圖補救你穿越平行世界所造成的損害。
我想,最終,你我都得為我們所做的事、造成的後果付出代價。
※ ※ ※
最後一次見到你的時候,我的肉體已經死去,殘存的只有意識。
儘管這仍是我計畫之中的事,但能夠和你再度共用實驗室,我得承認那帶給我超乎預期的愉悅。
你從收藏的黑膠唱片裡找出Supertramp在1977年發行的專輯。我不確定這是當年我送你的那張唱片,還是後來你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。
我看著你吞雲吐霧,從你的手上接過我們共享的那根香煙。
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,在我們還很年輕的時候,有一次,你看到我在捲大麻煙,你說你從來沒有這樣抽過大麻。我知道你通常用的是水煙斗,所以我笑說那是因為你不會捲煙的緣故。
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會說出那句話:「我猜,你也從來沒有這樣抽過。」語畢,我小心翼翼反叼住煙,避免點燃的煙頭燙到自己,同時朝你靠近。
你沒有猶豫,湊了過來。當你含住捲煙吸氣的時候,你的嘴唇和我的嘴唇輕輕相碰。
我猜你從來都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。
實驗室的母牛Gene適時哞了一聲,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把我帶離回憶。
我隔著眼鏡瞪著牠,想到除了腦死的病患之外,或許牠也能成為我的意識的宿主。
「William?」你盯著我,彷彿一瞬間看穿我的念頭。
我們相視而笑。
「……就算我們能夠成功把你的意識轉移到Gene身上,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得考慮。」你一面順著母牛的毛,一面對我說。
「我們可以透過腦波溝通,」我回道:「你得把我接上腦電圖的儀器,解讀我的思維。」
「就算那行得通,然而……我還是得幫你擠奶。」
我盯著你憋笑的臉,說:「我們可以指派Astrid。」
我們再度相視而笑。
※ ※ ※
Walter,我相信你一定記得我從來就不喜歡說再見。
我想,等到我消失之後,你才會發覺這就是我說再見的方式。
我所求的,其實並不多……
Give a little bit
Give a little bit of your love to me
Give a little bit
I'll give a little bit of my love to you
There's so much that we need to share
So send a smile and show you care
I'll give a little bit
I'll give a little bit of my life for you
So give a little bit
Give a little bit of your time to me
Give a little bit of your love to me
Give a little bit
I'll give a little bit of my love to you
There's so much that we need to share
So send a smile and show you care
I'll give a little bit
I'll give a little bit of my life for you
So give a little bit
Give a little bit of your time to me
~Supertramp “Give A Little Bit”~
The End
A/N2:William Bell和Walter Bishop相遇的場景改寫自官漫內容,當時Bell在聽的歌是Sly Stone的'Thank You'。
#317,Walter和Bell!Olivia在實驗室,背景音樂就是'Give A Little Bit'。
Fringe的主要角色我都滿喜歡,雖然第四季已經被我直接歸為爛尾作,但我想我還是會找時間補完第五季,有始有終。而且John Noble的演技相當棒,看他演Walter本身就是一種享受。
第二季季末,Walter和Bell在速食店鬥嘴那段讓我在螢幕前翻滾,差不多奠定了我支持他們的立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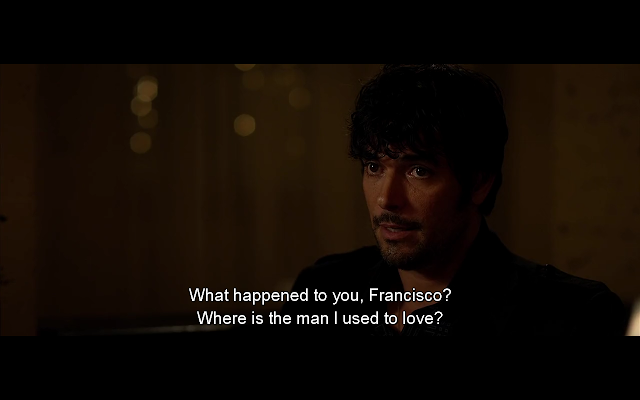
Comments
Post a Comment